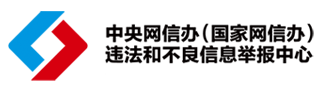来源:解放日报
作者:周程祎
时间:2025-03-10 10:09:18
访谈嘉宾:
高小玫 全国政协常委、民革中央原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
从高中升大学,毕业后即工作,对绝大多数人来说,按部就班地遵循“社会时钟”,如此便是一生。
“有时候,暂缓一步,反而有利于更好地出发。”全国政协常委高小玫长期关注青年问题。她呼吁,“间隔年”对于我国青年成长教育方面的意义值得高度重视,自愿选择、自主安排的“间隔年”,可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,补缺社会体验,让年轻一代拥有更加充实丰盈的人生。
社会实践教育需要多样化探索
记者:“间隔年”概念进入我国已有多年,但接受度一直不高。您选择在今年提出支持“间隔年”实践、将其纳入教育体系,是出于哪些考虑?
高小玫:“间隔年”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青年脱离既定学习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,是进入大学或正式工作之前的一段社会体验时间,以旅行、义工志愿、打工度假等为基本形式。发达国家重视“间隔年”,普遍认为“间隔”有助于青年认识社会。
思考这个问题,首先是因为青年成长教育的需要。近年来,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愈发严峻,一段迥异于学习生活的“间隔年”,可助学生充分放电、释压,恢复好奇心、提升共情力,修复身心也唤醒学习的内生动力、激发出潜能,而这本就是教育的目的。
此外,社会实践教育需要多样化探索。我们听到很多用人单位抱怨,现在的学生能力与学历不匹配,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实践知识。获得这种以体验为特征的实践知识,正是创新人才成长最重要的一方面,需要社会实践去补充。实践教育,需要从学校教育之外着眼。推广“间隔年”,有助于丰富社会体验、触发兴趣点,在这个过程中,毕业生还有可能找到职业方向,以更良好的职业准备和就业心态顺畅地进入社会。
我之所以在今年提出这个建议,还有一点是因为当下大学生慢就业的现实需要国家层面的回应。我国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比例连年上升,慢就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“被间隔”。国家应将慢就业纳入“间隔年”实践,予以制度性支持,让慢就业族的“间隔”实践成为成长成才、价值提升的过程。
支持“间隔年”与稳就业并不冲突
记者:很多人将大学生慢就业视为一种逃避就业压力的消极行为。按照您的观点,大家是不是应该换种方式看待慢就业?
高小玫:对,慢就业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、无意识的“间隔”,还含着一种不甘。面对慢就业,不能简单粗暴地批评,除了千方百计帮助有就业意愿的慢就业群体就业,更要正视它,而不是否定它、急于消除它。要承认慢就业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合理性。如果一定要有这种间断,就让这段时间发挥出积极的、无可替代的作用,把被动“间隔”化为积极“间隔”。
记者:从这个角度来说,支持“间隔年”与稳就业并不冲突。
高小玫:“间隔”不是权宜之计,而是为了让个人得到更好的职业准备、企业得到优质的劳动力。“间隔年”不会增加就业的不稳,而是让那些不急于就业者更安心、完善自己。
需要指出的是,我所认为的“间隔”,是自愿选择、自主安排的,不是“间隔”一辈子,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走“间隔年”的路。但“间隔年”确实对大学生等群体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,通过开拓视野、学习技能,明确人生规划,更好融入社会。从长远看,也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。
推行“间隔年”还存在哪些问题?
记者:在我国推行“间隔年”,还存在哪些问题?如何解决?
高小玫:问题方面,一是知晓度低,社会接受差。“间隔”休学、慢就业可能会被贴上“不务正业”“啃老”的标签,本人则难免有人生脱出既定发展轨道的恐惧。二是参与面窄。现有社会组织及基金的类似项目,属零星点缀式、象征性,鲜见财政支持,可享学生寥寥。三是制度政策不配套。如休学学籍管理不友好、有过“空窗期”再就业会面临质疑等。
最根本的解决之道,还是要调整观念,积极对待“间隔年”。可以将“间隔年”纳入教育体系,作为与学校教育并行的一种社会教育安排。对大学入学前、毕业后甚至学期中,学生自主的“间隔”申请给予支持,让“间隔”时间坦然进入求职简历,让学生安心“间隔”。
制度、政策调适配合也很重要。建议研究建立国家“间隔年”基金,以学校和社会组织的“间隔年”项目,为“间隔”生提供必要的经济补贴;解决“间隔”期的学籍保留和就业政策中的应届生身份问题,消除因未当期就业产生的心理落差和社会压力;将“间隔”实践与职业培训、技能学习等结合,让处于“间隔年”的群体也享受促就业各类政策。
此外,还可引导学校支持和社会参与,鼓励企业及社会各类组织提供“半工间隔”机会,如以工换食宿、义工志愿者等岗位;支持社会开展“间隔”体验服务,如“间隔”咨询、“间隔”旅行服务等;支持建立“间隔”相关的社会组织和机构,承担项目管理和培训等。


 沪公网安备31010502000374号
沪公网安备31010502000374号